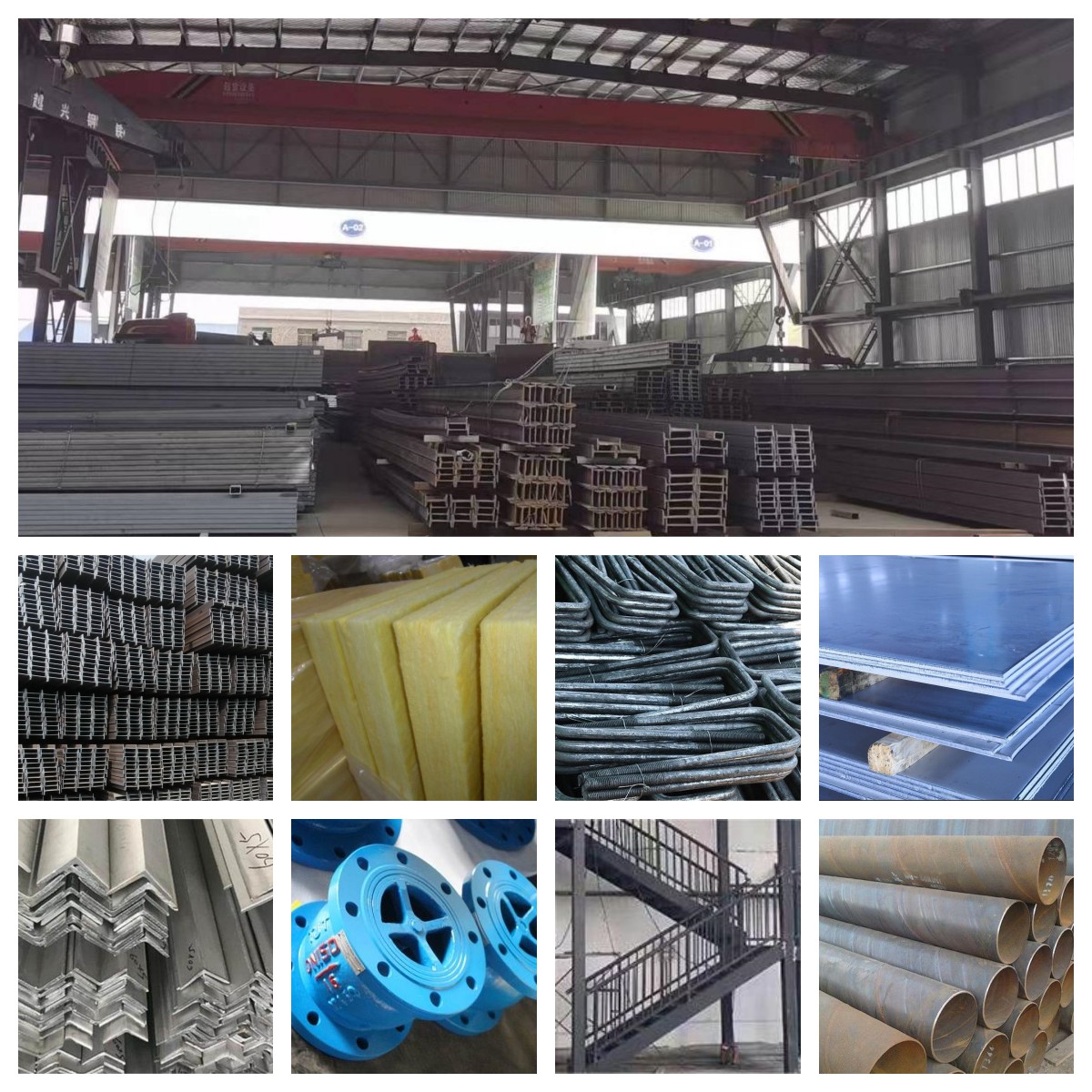灾难伤害了所有人,但遗憾的是,女性过得还要更难一些

危机过后,女性工作经历未长,年龄反而增加,因此,当其重新回到就业市场时,无疑更加处于劣势。
“如果你去摆摊,能卖些啥?”
一夜之间,“地摊经济”成了热词,网友们热热闹闹玩起了“全民摆摊”的梗,小商小贩们也抓住时机参与到这份经济建设中。

济南400户摊主车队开进夜市
然而这股新热潮背后,是我国在疫情后所面临的严峻就业形势的事实。
事实上,疫情爆发以来,在世界范围内,职场人、尤其是女性劳动者的工作状态都受到了冲击。
根据韩国2月份就业统计数据,在今年1月份申请临时休假的职场总人数中,女性职员占比为62.8%,远超男性;不仅如此,韩国20-30岁的女性工作者,其就业率的降幅亦最大,而同一年龄段,男性就业率反而略有回升。

不仅是韩国,澳洲、加拿大等地,女性就业率骤减的现象也正在同步发生。仿佛世界范围内,“女性衰退”伴随着经济衰退一并到来。
实际上,在过往历史上,1997年和2009年两次经济危机时,女性就业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相似的结果。
为什么在经济衰退时,一再被牺牲的总是女性?

风中有朵“失业”的云
韩国女性申请临时休假的意图,并不难理解。
和国内一样,由于疫情的存在,韩国政府延长学校停课时间,众多教育、托儿机构大门紧密,家庭成为大小孩子们撒欢的场所。一般男女双职工的核心家庭,急需调拨人手“暂时”返回家庭照顾孩童。
不过,由于疫情对线下业态冲击之巨,大部分企业均采取节省人力的方式,其主要表现就是裁员、减薪。这导致的结果即是,上述的“暂时”回归家庭,变成了长时段的“失业”,部分企业也乐于顺势而为。
韩国2月份就业统计数据显示,韩国20-30岁女性工作者就业率下降了1.7%,而同年龄层次男性就业率反而上升了0.2%。虽然20-30岁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性群体,但从这一数据我们足以窥见,韩国女性头上已然笼罩着失业阴云。

图/视觉中国
同样是东亚文化圈,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略有上升,1-4月份,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54万人,与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05万人;4月份,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.0%,比3月份上升0.1个百分点。
不过这一数据,并未区分男女失业率具体占比。但与韩国相似的是,国内部分地区曾做过如下倡导,即允许双职工家庭其中一人可适当请假在家陪孩子。
虽然大部分地区并未对具体性别作出界定,但最终实施的结果是,女性似乎毫无意外成为那个被远离工作的人。
今年2月,山东济南就曾“直白”地发出倡议,家中有低学龄且无人照看子女的双职工家庭,延迟开学期间可以女方为主向企业提出在家看护未成年子女的申请,切实解决双职工家长的实际困难。

不只是东亚文化圈,据澳洲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,3月中旬至4月中旬,澳洲女性的就业人数下降了8.1%,而男性下降了6.2%。
在北美,情况同样不容乐观。5月中旬,加拿大媒体Global News报道称,相较于男性就业人数下降了14.5%,女性同一数据比例高达17%。同时,15-24岁之间的女性受冲击最大,其就业率下降了38%。

美国人民排队领取失业补助
在经济衰退时,女性职场人往往遭受更大的负面影响,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。
现象背后,是女性一直以来面临的职场之困。

父权制的圈套?
上述女性“失业”群体,实际上大致分为两类,一类是单身失业女性,另一类则是为家庭所挂碍、最终失业的女性。
在这场面对疫情的持久战中,后者在员工-母亲角色之间所呈现出的张力,更值得关注。
在前现代社会,男女分工相对明晰,从“男主外女主内”、“男耕女织”这些习语中,我们至今能够看出其大致分工情况。

随着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发生,社会分工逐渐成熟,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,其在职场上的表现丝毫不逊于男性。
但在主流舆论气候中,女性传统形象的话语依旧占据主流市场。
昔日那个在家庭中默默奉献的“伟大的母亲”,如今拥有了更广泛的意涵——从“上得厅堂、下得厨房”,到“上得了班、带得了娃”。换言之,女性从单一家庭主妇的角色,向家庭主妇/母亲-职场人多元角色转变。
即便如此,在职场上,女性依旧遭受各种偏见。女性在招聘、升职等环节,相较于男性所处的劣势地位,显而易见。毕竟,在企业看来,一个没有“月假”、没有“产假”的男性,似乎是一个更佳的劳动力选择。
这些还不够,正如正文所提及的大背景。当危机/经济衰退来临、家庭亟须人手时,女性似乎又成了那个被牺牲的角色。而此种牺牲,甚至被美化为对于“伟大的母亲”的诠释。
危机过后,女性工作经历未长,年龄反而增加,因此,当其重新回到就业市场时,无疑更加处于劣势。这就意味着,从薪水这一单一维度看,妻子收入将始终低于丈夫,在家庭中的话语权也将一望而知。
在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》一书中,日本知名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将女性从家庭到职场-中断职业回归家庭-再返回职场的周期,称为“中断-再就业”型生命周期。

她认为,“中断-再就业”型女性的生活,看上去对女性有利,但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有利。
这是因为,对资本主义而言:
第一,可以把结婚前的女性作为快销劳动力,并过河拆桥;第二,可以以低廉的薪酬,雇用作为未成熟劳动力的中断-再就业型家庭主妇劳动力。
对父权制而言,这样可以确保丈夫在育儿期间拥有免费专职育儿妻子,在进入后育儿期之后,丈夫也可以不负担任何家务劳动,还可坐享女性带来的额外收入成果。
而那些陷入“中断-再就业”型生命周期的女性,虽然在表面上获得了“事业家庭双丰收”,但实际上家庭(对于育儿等家务的无偿劳动)和事业(经一再打断而发展平平的职业生涯),在本质上成为其双重负担。

图/《坡道上的家》
当然,疫情之下诸多女性回归家庭亦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。在经济平稳运行时,诸多家庭在实践层面将育儿的部分工作交给“市场”,如请家政上门等。而当整个就业盘子面临挑战,部分家庭收入缩水、无力再购买市场服务时,暂时回归家庭似乎是一项划算的买卖。
不过,为何回归家庭的多是女性?
从纯薪水角度考量,那些暂归家庭的“母亲”,在多大比例上实际上薪水反而高于仍在职场的父亲?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传统意义上对于“伟大母亲”的想象?
女性争取权利,是一场漫长的革命。即便是以民主著称的、至今被视为黄金时代的古希腊时期,唯有男性拥有投票权,而女人连同奴隶一起,被排除在外。
回到就业议题,我们常说,就业是最大的民生。
无奈的是,对于广大女性而言,在就业路上,不仅要面对那么多难以规避的机制性“陷阱”、与根深蒂固的歧见,还要时刻警惕种种社会结构性力量的蛊惑。
而在危机之下,全球范围内女性同胞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,更让人警醒,虽然世界范围内女性解放运动层出不穷,但现实依然骨感,仍需不断努力以逼近理想之丰满。
P.S. 本文观点仅代表特约作者个人观点,部分图片来源网络。